 摘要:
...
摘要:
... 灰娃,原名理召,祖籍陕西临潼,1927年出生于“八百里秦川中部,一个绿荫掩映、泉水琤琮的村庄,未及记事年龄随双亲到了古都长安。父亲在中学教书,母亲在家操持家务”。1931年入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读书,一直读到六年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灰娃随家人迁往距西安百来里之外的一个村子暂居。1939年,被姐姐和表姐送往延安,进入“延安儿童艺术学园”学习音乐和戏剧,从此开启一段崭新的人生旅程。当时的延安不仅是战争的后方,还是文化艺术的“大后方”,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比如艾青、何其芳、严文井、冼星海、杜矢甲、张仃、蔡若虹等,灰娃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文化艺术熏陶。1946年,灰娃与八路军新四旅作战参谋武昭峰结婚,随部队转战晋冀鲁豫地区。1948年,患肺结核前往南京治疗,1951年转至北京西山疗养院,同年,丈夫武昭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5年,灰娃身体初愈,考入北京大学,曾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1960年被分配到北京编译社做编辑,后又因病提前退休至今。1964年,与开国少将、战争史专家白天结婚,这段婚姻持续到1974年白天因病逝世。1966年“文革”开始后,灰娃陷入了精神分裂,持续六年之久。

灰娃
1972年,在医生看来,灰娃已经恢复健康。但外人无法真实“勘探”出她内心深处的恐惧、疑惑、愤恨、绝望和悲凉,于是,寻找心灵出口的她尝试通过写诗排遣悲情。最初她为自己写的“东西”感到恐慌,私下猜想着肯定有人会用什么新式武器探测到她写诗的秘密,她常常把刚写完的诗作撕掉、扔进马桶冲掉。这种边写边撕的状态直到被张仃发现才停止。张仃是灰娃在延安儿童艺术学园求学时的美术导师,新中国成立后因同住北京,经常来往,他及时、敏锐地捕捉到灰娃的诗才和灵性,并建议她将内心美好的感受写出来,把诗当作美的出口。受到鼓励的灰娃从此将写出的诗装在铁盒子里,埋在花盆下,直到1977年春,她才敢把诗稿取出来示人。这段时间保留下来的诗作有《大地的母亲》《无题》《心病》《路》《水井》《我撒手尘寰……》《土地下面长眠着——》《墓铭》《我额头青枝绿叶……》《不要玫瑰》《只有一只鸟儿还在唱》《我怎么能说清》《带电的孩子》《童声》《己巳年九月十二日》《鸽子、琴已然憔悴》《穿过废墟 穿过深渊》等。
灰娃曾言:“我所有的文字,都是我的生命热度、我情我感体验的表达。”灰娃开始写诗时已经45岁,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写作经验,但人到中年的她借由诗歌得以释放内心的焦虑,从精神危机中逃脱出来,获得了灵魂的自我拯救。自此,灰娃矢志不渝地在诗歌写作生涯中砥砺前进,持续创作的热情至今未尽,每一首诗的创作都带给她“心灵洗礼的感召震撼”,恰如她创作于2020年的《带着创伤心灵的芬芳》一诗所写:“难得的日子,仿佛一只相思鸟儿/躲进荼靡花丛幽寂阴影/与自己聊天、忆往,夜夜走入无从察觉/销蚀关于人、关于灵魂记忆的噩梦/被经受污名、人性摧残穿越时间/感恩宇宙大神赋予我向神靠拢天性/独自和天使的忧郁哀咏低涌于废墟/暮霭里神的信使夜莺、秋水仙的歌/神秘、空灵、忽隐忽现振荡于苍穹深处/你听见心灵洗礼的感召震撼吗”。在与命运的沉浮相逢时,她“逆风前行,携带觉醒激情”(《那琐细无名的思念》),并及时记录下每一个“短暂的诗意体验”(《带着创伤心灵的芬芳》)。她警示别人和自己,“梦碎之人,莫把年华耗尽”,“听那自由歌后百灵之春时隐时现/隔溪余韵悠扬飘忽/星星之火也在扩展光焰”(《怀乡病》),或者选择“神一样,从冰蓝的光气穿越/沉浸在迷迭香灵芬的神秘清馨/听自己良心以沉默言说”(《愿命运依然见证》)。“我最初的梦,我依然爱/我的星辰,照临我第一束光/唤醒我的牵挂,我的眷恋/我的爱与痛,我的怕与惊……”(《绿天堂》)灰娃的人生经历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如果说她的前半生是站在“信风中/喂养沉默无花的果实”,她的后半生则是“织一袭骑马来的春光/整个大地全通向彼此”(《山山》)。她的诗歌不仅“可以看作是她‘一个人的心灵史’”,还在当代诗坛上具有特殊意义,研究和考察她的诗歌创作历程,无疑具有文学史的意义。
灰娃的个人经历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延安时期的童年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期间精神分裂时期;新时期与张仃结为伴侣;张仃逝世至今。灰娃自“文革”后期开始写诗,她每个人生阶段的诗歌创作都如其创作于2019年的《怀乡病》一诗中所言,“生命密码已编织成斑斓悠长的日子/铭刻在心上,谱写在歌里”。
时代的病症:“我鬓角额前星星缀满”
灰娃于1966年患上精神分裂症,70年代在患病的情况下非自觉地开启了写作生涯,在此之前灰娃几乎没有写作经验。最初,诗歌创作对她来说是释放内心焦虑的一个出口,是治疗病痛不可或缺的“良药”。因为诗歌,她得以在非现实的世界中找到灵魂的寄托,最后竟神奇地从精神分裂的危机中康复,她的诗歌带给读者心灵的洗礼和美的享受。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灰娃的诗歌创作属于幻觉型艺术,她本人则是典型的“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诗人,她是鲜有的在不自觉中完成个人主体性回归的创作特例。
灰娃在少年时期经历了残酷战火的洗礼,也接受过红色革命教育,从成长经历看,她应该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投入新的学习和工作。但真正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她反而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当时的大环境格格不入。进城后,灰娃发现她周围的环境和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实的力量对于从儿时起就喜欢对着星星、银河歌唱,喜欢睡在自己种植的花草旁边的灰娃来说是一种精神的践踏,她无法从根本上接受虚假的“真实”。
社会现实的状况令灰娃费解,她的单纯、敏感、特异同样令一些人无法理解和接受。日复一日,紧张的神经终于绷不住,灰娃陷入精神分裂。“文革”开始之后,她愈发不堪承受压抑,为了排解苦闷,她不由自主地把郁积于心的感想写下来。从荣格对精神病人的分析可以找到灰娃发病的根由:“精神病理学告诉我们,有一种精神紊乱就是起自病人把自己与现实割裂开来,越来越深地陷入他个人的幻想之中,结果,现实力量的失势导致了内心世界决断力的增长。”思考空间被规约、观点被束缚,而诗人灵魂里却充溢着澎湃的情感,不断涌现出来的矛盾不时冲撞她敏感的心扉。最终这些情感借助诗歌表达出来,淤积在诗人心中的愁思乱绪得到了疏通和释放,焦灼忧虑的心灵在诗的世界里获得暂时的安宁。
灰娃自小就“朝思暮想着两件事:旅行、作曲。将心灵对大千世界的奇妙感悟诉诸管弦。幻想中自己应是贫苦的,买不起蜡烛,月光下坐在屋顶上编织音乐”。如此浪漫的理想只属于纯真美好的心灵,她始终葆以质朴之心捍卫世间的“真”和“美”:
我鬓角额前星星缀满
我为厚道的心呼号用嘶哑的嗓音
即使世间没有感应没有回响
也压根儿就没有真这件事情
——《墓铭》
诗人在现世中无法诉说无限的伤心委屈,只好转身,背对悬崖迎着黑暗独自上路:“生而不幸我领教过毒箭的分量/背对悬崖我独自苦战”(《墓铭》)。无论是被毒箭重伤,抑或被曾经的信仰欺骗和遗弃,诗人都陷入了孤独的绝地。在现实生活中,生命受到禁锢,精神得不到自由,追求美而不能,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促使灰娃拿起笔,诗歌成为精神的避难所,使受难的灵魂得到慰藉。
“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虽说“文革”中很多诗人都有着坎坷的人生际遇,但像灰娃这样为寻找灵魂出口而不自觉拿起诗笔走上自我救赎之路的创作行径尤显特异,这些文本为当代诗歌史提供了别样的视域,也打开了女性诗歌写作的新面向。
诗神的眷顾:“我们蹒跚人间紧拥磨难”
灰娃开始诗歌写作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写作经验。当愁绪和郁闷无法排遣时,她才开始随意涂写,从一个字、一个词到一个短句、一段话、一首诗……逐渐地积累下来,直至后来结集出版,这也是灰娃被视作“自我教育”下的“素人诗人”的原因。荣格曾阐释艺术和艺术家的关系:“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力,它抓住一个人,使他成为它的工具。艺术家不是拥有自由意志、寻求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自己实现艺术目的的人。”灰娃就是一个被诗歌之神“抓住”的人,她自觉而清晰地诠释过自己的创作心理和写作过程:“某个时候,心里有种旋律、节奏显现,不知不觉日益频繁在心里盘桓,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事,这音乐总挥之不去,音乐执意占据心灵,控制心灵。隐约中有异样感觉,这时,受此音乐催促,以文字释出,呈示为人们称之为诗的这种形式。然后删改,尽力改好些。”灰娃的诗不落俗套,浸透着神秘韵味,诗才天赋处处流露。
纵览中外女诗人的创作历程,诗总是与青春结缘,茨维塔耶娃18岁时就自费出版了诗集《黄昏纪念册》,阿赫玛托娃23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冰心读大学期间就结集出版了小诗集《繁星》和《春水》……古今多少才华横溢的诗人年少时即自觉以诗练笔,写作风格在创作中也逐渐成熟。灰娃则不同,她中年开始写诗,自始即形成了比较成熟稳定的风格,即她写诗先形成诗的旋律或节奏,然后跟随着它们再将诗情或诗思落于笔端。诚然,与当代很多女诗人相比,灰娃不是多产的诗人,因为她的每一首诗都来自灵魂深处,唯心灵受到牵动方能起笔,并带领我们走入一片无人到访过的奇异境地。
天生的敏感细腻注定了灰娃的孤独和寂寞,这导致她一度成为常人眼中的“另类”。她曾在诗中暗示过她与现世的无法沟通:“我们的手臂□人说是钟情热切/我们蹒跚人间紧拥磨难/过路者都把这浩大悲壮/把这隐痛□轻笑闲谈”(《路》)。
诗人见识了生活中叠加的虚假与谎言,满腹的委屈和“隐退”之心无法向俗世里的人们倾诉,一颗本真质朴的心笼罩在浓重的孤苦烦闷之中,因而有诗句“我们蹒跚人间紧拥磨难”。但正是这“孤独与寂寞,对外有助于默观默查,有助于更深沉更冷静地观照社会;对内有助于自省反思,彻悟人生,凝聚内心的生命力”,使得诗人对自己曾经坚守的信仰、对现实和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缪斯选择了灰娃,把灰娃引入诗的苗圃,犹如种子遇到阳光和土壤,又如同泉水找到流泻的出口,诗人终于为自己内心积蓄的焦虑和形形色色的美找到了倾吐的渠道,她凭借精神直觉直抵作品深处,挖掘分裂的自我和驳杂的情感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她对内心幻象的正视和处理也是她对自我生命的反省。
结语
灰娃的特立独行不可复制,她的诗风在当代诗坛极具标识度。其诗歌风格既奇丽又矜持,审美既古典又现代,诗品既清明又神秘,思想既单纯又丰厚,感受既奇诡灵动又充满人间烟火气,艺术表现手法既浪漫又超验,语言既凝重苦涩又清峭唯美,想象既无拘无束又充满野性。她因患病写诗,因诗而从精神病态走出,生命力愈发强劲,她的诗歌写作可以看作是对权力话语控制的反抗以及自我治疗。她在这种“治疗”中创造出一种全然个性化的诗歌话语系统。尤为可贵的是,九十岁高龄时,她仍坚持写诗,在诗歌题材、意象、风格和表现力等方面均有新变。从小到大,灰娃“心里就装着一个字——美”,创作四十余年,她笃定地秉持着自己的诗歌观,创造出神秘瑰奇的生命境界。灰娃的诗率真,具有摄人心魄和精神自救的力量,她为女性诗歌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

本文节选自《漂往远海:中国女性诗歌史(当代卷)》(孙晓娅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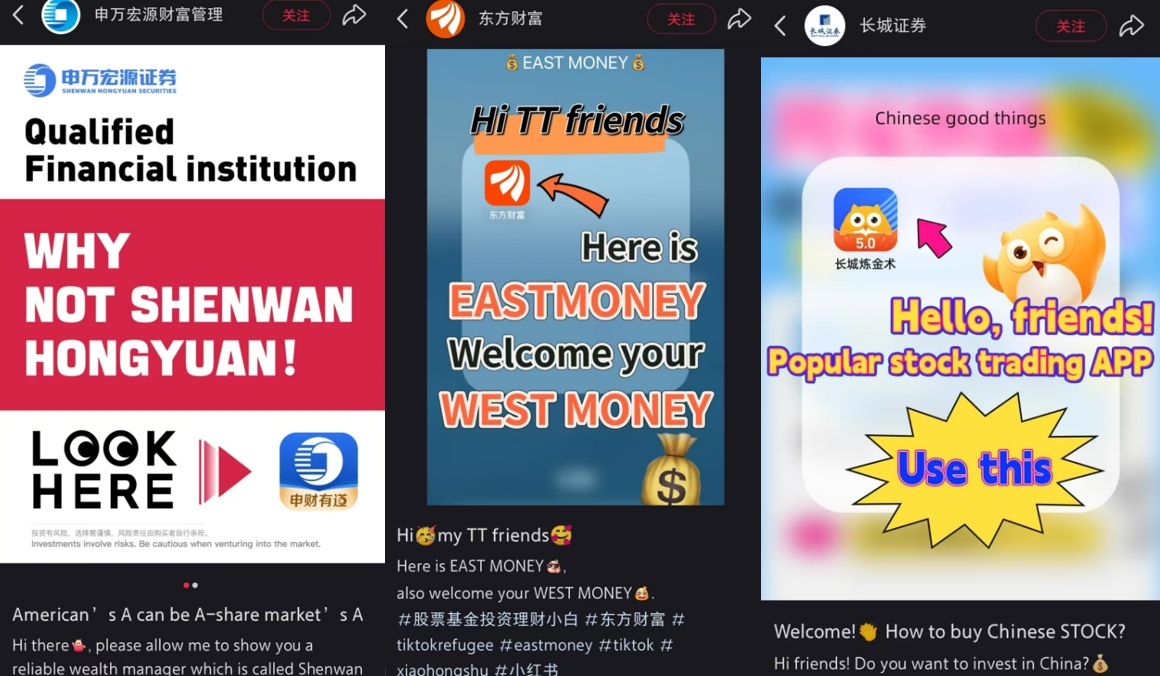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