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摘要:
... “对付敌人要比对付朋友来得简单。”——乔治·凯南
人们常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在今天这个二战后国际秩序即将崩坏的时代,这里讲的是一段特定国际秩序当初怎么建立的往事,以作纪念与警醒。

1949年4月4日,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十二国在华盛顿签订北大西洋公约。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签约仪式上发表讲话。
一
二战之后的国际关系,有一个东西是始终绕不过去的:核武器。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话来说,就是核武器“改变了所有的问题,也改变了所有的答案。”( 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577页)核武器放大了所有国家的恐惧与猜疑。没有核武器,国家安全自然得不到保障,可有了核武器,也并不就高枕无忧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政治喜剧《是,首相》中有这么一段:
新任英国首相吉姆·哈克会见了一位教授。教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哈克是否相信核威慑这回事,哈克回答说是的。
“为什么?”教授追问。
“因为……它产生威慑作用。”
“威慑谁?”
“俄国人。不能让他们进攻我们。”
“为什么?”教授询问为什么威慑力量能威慑俄国人,不让他们进攻英国。剧中的首相哈克回答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发动进攻,我会按(核按)钮。”
“您会吗?”
“哎……”哈克犹豫了一下。“我会不会?”
“唔……您会吗?”
“作为最后一招,我会。肯定会。”哈克又想了一下说,“至少我认为我肯定会。”
教授追问:“那么最后一招是什么呢?”
哈克回答:“如果俄国人侵犯西欧。”
教授微微一笑:“可是您只有十二个小时来作出决定。所以最后一招也是首先的反应,您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
教授缓了一下追问:“好吧,您不用担忧。俄国人为什么要试图吞并整个欧洲?不,如果他们要干什么,那将是萨拉米香肠战术。”教授接着假设在西柏林发生暴乱,建筑物处在火海之中,东德消防队越过边境来救火。“他突然停止踱步,瞪眼看着我,并问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不会按钮。很显然,答复是不。罗森布拉姆点点头。他看来表示同意。然后他问我如果东德警察与消防队一起进来,我会不会按钮。我又摇摇头。我怎么可以由于这样一个小小的领土侵犯行动而发动一次核战争呢?罗森布拉姆又踱起步来。在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乔纳森·林恩、安东尼·杰伊著:《是,首相》,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79-80页)
“假定东德人派遣了部队,随后再增加部队——他们说不过是为了控制暴乱。接着俄国部队来替代东德部队。您会按钮吗?”哈克继续摇头。再接下来教授假设俄国部队被“邀请”留下来支援民政管理。接着,西柏林被切断。哈克被询问是否会按核按钮,哈克无法给出答案。
“行,现在讲设想二。俄国军队的策略‘出于偶然’,使士兵故意越过西德边界……这是不是你所说的后一招呢?”
“不。”
“设想三。假设俄国人已经入侵和占领了西德、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再假设他们的坦克和部队已经到达英吉利海峡。再假设他们已布置就绪,准备入侵,这是不是后一招?”
哈克回答:“不。”
“为什么不?”
哈克支支吾吾地说道,“因为……我们只能为了自卫而打仗。用自杀的办法,我们又怎能自卫呢?”“那么,什么才是最后一招呢?”那位瘦小年老的教授微微一笑。“皮卡迪利?(伦敦的商业区)”
以上的场景虽然是喜剧,但其中描述的逻辑却非常真实。核威慑的可靠性(或者说不可靠性),曾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政学两界的讨论焦点。基辛格还没有执政之前,就是凭着描述北约中的核难题,才在欧洲国家声名鹊起,成为列国政府的座上宾的。《是,首相》里面这位教授的原型,很显然就是基辛格自己。
核威慑不可靠,核同盟(所谓延伸威慑)就不可靠。面对拥有强大核武器的共同对手,一国的核武器能够遮护住自己的盟国吗?它会为了盟国的安全和利益让自己冒核毁灭的危险吗?
二
本来在任何时代,同盟都有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倾向。温斯顿·丘吉尔有次恶毒地说道:“(同盟)就是相互指责、反唇相讥的一种练习。”(Michael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51)基辛格则坦陈:“要联合多数国家聚集力量的企图常常同彼此目的不同相冲突,集体安全体系的范围越广,参加者的动机就越复杂多样,采取共同行动就越困难。”
核武器为这种紧张关系火上添油。核战争的巨大危险使得盟友之间相互援助的承诺的可信性受到质疑。要应付核战争危险,也要求对一个国家不仅要严格控制自己的核武器,甚至也要控制其他国家的政治、军事决策程序,而这无疑是对其他国家主权的一种冒犯。
在五十年代以后,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其实北约国家都在犯嘀咕,北约到底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美国人会不会在战争的时候使用核武器来做防卫。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1959年,美国国务卿赫脱面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道:“我不认为总统会让我们卷进一场全面核大战中去,除非我们自身也有遭到毁灭的危险。”(Dean Acheson, “The practice of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Vol.41, No.2, 1963, pp.251-252) 当时的一位法国将军皮埃尔·加卢瓦宣称:同盟已经完全丧失了其自身的意义,核武器已使同盟过时(皮埃尔·加卢瓦著:《美国战略与欧洲防务》,载于亨利·基辛格编:《国家战略问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290-312页)。法国人一再重复这句话:Le nucleaire ne se partage pas——核武器只保护它的持有者。所以,基辛格总结道:“现代武器的毁灭性造就了(同盟国家退向)极端民族主义或中立主义的倾向。”(亨利·基辛格编:《国家战略问题》,160页)
那该怎么办?
一个办法是让大家都有核武器,自己保护自己,这样就不怕别人抛弃自己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就是这个想法——法国必须有它自己的核武库,才能防止盟国(美国)的抛弃。美国人多多少少同意戴高乐的这个忧虑有道理,肯尼迪曾经在1963年预期十年内世界上将会出现十五到二十多个有核国家,其中大部分会在欧洲。
但这么做有几个坏处。首先,单纯讲经济,在北约内部发展美国之外的独立国家核力量是一种重复浪费。而且,核武器是很花钱的,把钱都花在核武器上了,常规防务力量能够获得的资源就少了。
第二,每个国家都有核武器,不代表这个国家就有一支可靠的核力量。一颗两颗核武器根本就不够,数量必须到一定规模,还要有合适的运载工具,否则这些核武器很容易被先发制人的攻击全数击毁在地面上,没法进行核报复。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小国家很可能在冲突一爆发的时候就把核武器先用出去,从而大大地增加了核战争爆发的几率。
第三,从指挥与控制的角度讲,如果大家都有核武器,那该怎么协调控制呢,威慑失误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假如发生苏联的威胁,前方的国家出于生存考虑,可能声色俱厉,拿着核武器虚声恫吓,苏联会不会被吓住不知道,但后方的北约国家很可能被前面的盟国吓住。一位美国官员坦陈:“我们之所以反对(欧洲)国家核力量的基本原因,与其说是他们不起作用,还不如说是我们并不希望违反我们的意愿的情况下被牵进一场核战争中去。”(基辛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核难题》,载于戴维·阿布夏尔、理查德·艾伦主编:《国家安全——今后十年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342-343页)
第四,当时还必须考虑到“德国问题”,德国要不要有核武器?德国虽然是新欧洲的栋梁之一,却也是被猜疑的对象。有一次基辛格面见戴高乐,戴高乐向其陈述他对未来欧洲的设想。基辛格请教戴高乐有何妙计来阻止德国人主宰他刚描绘的欧洲,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费唇舌详尽做答,只答道:“透过战争啊!”此时距离戴高乐与阿登纳签署德法永久友好条约不过六年(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555页)。 有核武器的德国不仅会在欧洲国家内引起惊惧,也会让苏联和华约其他国家紧张万分,二战毕竟过去才没多少年。
最后,让大家都有核武器,说到底,就是承认对同盟没有信心。而一旦承认,大伙军心士气的沮丧也是不得了的。
还有一个虽不是问题,但却也不得不考虑到的因素——大家没有经验。“核武器是如此的威力巨大,而关于如何管理、控制和使用这种武器的国家以及国际经验是如此的有限,同其他有核国家进行谈判达成协议是如此的费劲,因此任何改变核现状的行动都让人忧心忡忡。”(Michael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64)
总而言之,让大家都有核武器的想法虽好,但却仍然不是上策。
三
那当初北约是怎么渡过这个难关的?
关于这个问题,后人的答案不一。
第一个答案是说,东西方关系改善,外部压力减轻,让北约国家之间少了争吵。这主要指的是六十年代之后,美苏双方开始尝试接触妥协。从1963年开始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开始,东西方陆续在1963年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又签订了核不扩散条约,1972年又重开限武谈判。1969年联邦德国提出了新东方政策,1972年起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战后欧洲边界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双方倾向于承认现状。
但是这个答案是肯定是有缺陷的。首先是时间不对。苏联对欧洲的核威胁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到五十年代晚期,由于赫鲁晓夫的大吹大擂,美国甚至产生了核优势已不在我的错觉,所谓“导弹差距”。如果说六十年代以后双方关系和缓导致北约得以保全,那么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十年呢?再者说,有学者已经指出:“缓和,北约与华约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其说是引起军事稳定的原因,不如说是军事稳定的后果。因为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感到安全,它们才能够寻求同共产主义国家达成有限的和解。”(Michael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71)换句话说,缓和极有可能是果不是因。
这里还有第二个答案:之所以北约还能保持完整,美国的核保护承诺还得到认可,是因为其他的选择更不受欢迎。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核战略的演变》一书中的结论是:“绝大部分盟国宁愿忍受它们所已熟知的美国核保障的不确定性,也不愿意去忍受独立核力量所会带来的政治和战略上的不确定性。英国和法国都发现很难说他们拥有核武器以后在外交上获得了什么好处,至于在军事上又给它们带来了什么好处仍然只能是主观臆测的问题。”(劳伦斯·弗里德曼著:《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385页) 简单来说,欧洲国家搞自己的一套,并不是一个受到欢迎的选项。
这个答案同样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假如说欧洲国家只是迫于无奈接受现实的话(也就是说美国出核武器,它们出常规武装),那么他们对北约的承诺程度似乎应该有下降才对。但事实是,六十年代以后北约欧洲国家纷纷加大了对常规力量的投入(John R. Oneal,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burden sharing in NA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3[1990]: 379-402),北约内部的核争论也趋于停歇。
既然这两个答案都不能完全解释问题,我自己的猜想就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让欧洲国家的核担忧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答案是核分享——美国人把自己的核武器拿出来,以某种方式给予了欧洲国家以一定的控制这些武器的能力与名义。
四
美国有个网络数据库“国家安全电子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在2003年发布了一个专题,名为“美国核历史:导弹时代的核武器与政治,1955至1968年”,该专题里面有大量的解密档案。以下内容多是根据对这些档案的解读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糅合而成(下文中未作注解者,多来自于此解密档案)。
由于核武器那可怖的威力,美国人一开始的态度是:严格控制,严格保密。1945年9月的一份公共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七成公众和九成国会议员反对与其他国家分享核机密。一位参议员表示:“无限期地维持核机密是我今生首要的选择。”在政府内部,大部分官员也持同样态度。杜鲁门自己也说道:“在法纪荡然的世界里,原子弹如若失控,将造成极大的危险。”(麦乔治·邦迪著:《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183页)英国虽然与美国共同研制核武器,但到了1945年11月,美国也终止了与英国除原材料领域以外的所有核合作。在整个杜鲁门政府期间,美国都坚决维持对核武器与核武器技术的垄断。
松动,是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的。1953年10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国家基本安全政策文件——NSC162/2。文件中记录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即“美国冷战的机会有赖于与自由世界国家结成可以信赖的联盟”。
这句话并不是后世那种虚言套词,而是艾森豪威尔的真实想法。1956年10月,当时的对外行动委员会主席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对艾森豪威尔说道,对美国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使欧洲保持虚弱和分裂状态,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弱者无法合作,弱者只能乞求。”(Gunnar Skogm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uclear Dimension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4, pp.30-31)
我们当然可以说,艾森豪威尔的这个回答是一种政治德性的表现,因为这是一种对“权力的诱惑”的克制。麦乔治·邦迪,日后是肯尼迪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有一个更闪烁着自由主义光芒的回答:“不是建立在同等权利上的同盟,而是单方面的依赖,对自由人的尊严和判断力都是有害的。”(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te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5-19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7)但在这里,我要解释的是,艾森豪威尔的政治德性是怎么跟他对现实政治、现实利益的考虑结合在一起的。
艾森豪威尔上台的时候,公开声称他“在经济事务上是保守派”(小阿瑟·施莱辛格著:《美国共和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370-371页)。在国内,他认为“政府过多的国防开支不仅会增加人民的负担,败坏人民的积极性,造成通货膨胀,而且会增加政府的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自由社会”(David L. Snead, the Gaither Committe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7-8)。对冷战,他的想法跟乔治·凯南一样,认为其是一项长期事业。认为“美苏哪一方能使自己保持经济与军事力童之间的均衡,那么哪一方就能最终赢得冷战”(Martin J. Medharst, Eisenhower’s War of Words, Rhetoric and Leadership,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58)。所以要削减防务开支才行。
那么,怎样才能减轻防务开支呢?艾森豪威尔的打算有两个:之一就是依靠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削减常规防务开支,这条路走下来就是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一旦苏联对欧洲开战,美国就会跳过常规防御阶段,直接用核武器进行全面还击。艾森豪威尔并不确信美国能够在第一次打击中解除苏联的核武装,也不是不理解核战争将会带来的巨大破坏 ,也不是相信核战争能够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所以他其实对核战争的可怕心知肚明,此不过虚声恫吓而已(艾森豪威尔觉得核武器主要是种心理武器);之二就是要从欧洲撤军。艾森豪威尔不止一次地对其政府官员说,美国的海外驻军只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艾森豪威尔还有次说:“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罗马,像罗马人那样用我们的军团守卫着遥远的边界,这些边界,从政治上讲,不是我们的边界。”(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7)
但撤军归撤军,却不能只是把欧洲防务丢给欧洲盟军一走了之,必须有善后之计。第一计就是西欧一体化,只有欧洲国家聚成一体才有自卫之力。艾森豪威尔早在担任北约总司令时,就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1951年7月3日,他就建议成立欧洲联邦。在一次演讲中他说:“只要欧洲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各国居民便无法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应有的成就。各国间的国界对于他们的利益和合理的分工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影响了财富的沟通,助长了不信任心理,维护了既得利益。然而满足于目前而对未来的美好前景毫无向往的人们,是无法确保他们自己的安全的。只有以联邦的形式实现欧洲的统一,才能获得欧洲的安全,才能继续对西方的文明与进步做出贡献。”(让-莫内:《欧洲第一公民——让-莫内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416页)学者认为,艾森豪威尔有一个三步骤计划。第一阶段预期为五到十年,美国仍旧在欧洲保持一支相当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同时促成欧洲初步实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体化。在第二阶段,一体化中的欧洲将接手地面防务,美国象征性地保留一部分地面部队,但主要作用在于提供战略核威慑。在第三阶段,实现一体化目标的欧洲将完全依靠自己对抗苏联的威胁,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9)。
第二计就是提高北约的多边主义性质。由于艾森豪威尔实质上是在打算减少美国所承担的军事义务,所以他必须在另外一个地方对盟国进行补偿,那就是提升盟国在北约中的地位,授予盟国对北约事务更大的发言及决策权。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不应继续“将自己信任的盟友视为二等公民”(Steve Weber, “Multilateralism in NATO: 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 1945-1961”, p.41)。
无论是第一计还是第二计,在同盟中,美国放弃对核武器的独家垄断都势在必行。要加强欧洲的军力,没有核武器是不行的;为了使盟友乐于贡献,成为真正的伙伴,也必须给予他们以一定的自主权,其中之一就是对于核武器的控制。基辛格在描绘北约内部关系的时候,说“自相矛盾的是,大西洋地区的团结可能要依靠这样一种治理结构来促进,这种结构给予各国自由行动的空间,但是减少它们如此行动的欲望”(Henry A. Kissinger, "Coalition diplomacy in a nuclear age", Foreign Affair. 42 [1963], pp.541-542),也就是这个意思。
1960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说道:“从一开始……我就一直相信,我们不能拒绝给予我们的盟友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已经拥有的武器。”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考恩(John McCone)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一次会谈中,其意见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认同:“只要我们拒绝给予欧洲伙伴武器,我们就无法期望他们的主动性。”(Steve Weber, “Multilateralism in NATO: 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 1945-1961”, p.42)艾森豪威尔“准备向北约盟国提供他们防务真正需要的武器……(总统)相信如果拒绝向盟国提供对导弹及其弹头的控制权,就无法达到此种目的”(Steve Weber, “Multilateralism in NATO: 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 1945-1961”, p.42-43)。
在这里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冒险进行信任建设。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指出:“信任必须是双方面的。只有别人信任我们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向他们分配责任。”(NSC meeting, October 29, 1959, FRUS 1958-60, Vol.7, part 2, p.290) 对这句话,学者的解释是:“如果美国不愿意信任他自己的盟友,不将自己最重要的武器与之共享,(我们)怎么能期望欧洲人信任美国?”(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55)“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眼光看来,美国拥有所有的权力,因此也承担了所有的责任的这种情形,是不健康的,也是同盟中发生不安的根源。”(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92)
当然,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愿意放弃核垄断,也跟其核战略大有关系。正如上所述,美国此时的战略是大规模报复战略。杜勒斯在1956年末的时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时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盟友说,下一场战争如果发生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场核战争。由于他们没有核武器,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从我们的表态中得出,当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他们的位置是在一边作壁上观。这种态度无论对我们来说,还是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合适的。”(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6-183)杜勒斯总结说,那些没有自己核力量的盟友,因此就会觉得“他们没有发言权”,停留在一种“相当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慌乱”之中(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6)。因此为了同盟的稳定起见,必须给予盟友一定的核武器控制权。在1953年的时候,杜勒斯已经在开始谈论将核武器整合到北约军事力量中去的问题,目的在于使北约拥有属于自己的核能力(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7)。1956年,杜勒斯在同英国外相会面的时候,指出“战略就是打算让每个人都有核能力”。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的时候对杜勒斯也说:“核武器已经变得常规化,我们不能拒绝我们的盟友以这种常规武器。”(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8)1958年5月,杜勒斯再次表明美国应该在北约内部实现核能力的更大的国际化,“这就是最终答案,我们必须依照它行事,信仰这个信念。”
五
美国既然决定要放弃核垄断,分享对核武器的控制权,那怎么分享呢?
所谓的核控制权,是在三个层面展开的:首先是决定关于核武器部署与使用的军事战略应该走一个怎么样的渠道来制定,其次是谁有权来决定部署以及使用核武器,最后是政治机构与军事机构的联系应该怎样安排的问题(Paul Buteux,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Consultation in NATO 1965-19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8)。换句话说,核控制的过程既可以指实际上拥有核装置及其处分权,也可以指通过一定制度对核军事计划和决策施加有效影响,前者是硬控制,后者是软控制。因此,要分享核武器的控制权也就有相应的两个途径:硬分享和软分享。硬分享是保证北约非核盟国对核武器拥有某种实质上的所有权或控制能力,软分享则是提供有效的制度途径,使得非核盟国能够参与到有核盟国的军事计划的制定和决策中来,让它们可以影响核武器的部署与实际使用。
摆在艾森豪威尔面前的有这么几种选项:
第一种选项是鼓励北约各国自建其核力量。
第二种选项是转让选项,也就是将美国的核武器或者技术按照某种条件转让给单个国家或者超国家组织。这个选项比第一个选项好的地方是让美国仍然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些核武器的使用。
第三种选项是欧洲力量选项。也就是欧洲国家通过合作建立统一的核力量。
第四种选项是大西洋选项,那就是美国本身参与到一体化进程中来,将自己的战略、战术核武器置于统一的北约政治和军事结构管理之下。
在所有的这些选项中,第四项是最不可能实现的。“美国人虽然通过大西洋框架推进欧洲一体化,但是并不是真正希望实现大西洋地区一体化。”(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te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5-1997, p.148) 这件事显而易见,所以第四项选择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菜单中。
第一项又显得有些过激。无论是行政机构也好,还是国会也好,对于独立国家核力量多半都持反对意见。独立核力量所面临的困难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赘述了。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之前,NSC6017文件在对美国核分享政策回顾的时候,指出“不鼓励独立核力量的出现一向是美国核政策的基石”。
所以能用的就是第二项和第三项。艾森豪威尔自己更偏爱第三项。在这个方案下,德国的核需求会被安全地整合到欧洲联合中去,欧洲拥有统一的核威慑力量本身也会促进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体化。NSC6017文件指出:“美国认为支持经过选择的盟友发展核能力有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的目的在于)对其核能力的发展施加影响,而不是阻止这样的发展。”
六
以下的内容涉及许多细节,不耐烦的读者可以一目十行过去,不打紧。
最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内部还是有许多反对意见(尤其是原子能委员会)。所以艾森豪威尔要从边边角角出发撬动局面,比如首先修订原子能法(1954年),向盟国提供一部分核信息。一开始的借口是说,既然美国在欧洲部署了很多核武器,那至少要让欧洲国家知道这些武器的数量、特性、安全措施和使用战略和方法,方便他们配合。这些信息跟核武器制造技术没有关系,忌讳就会少一些。艾森豪威尔很显然是在采用切香肠战术稳步前进。
在1957年的一次政府会议中,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要求加强核信息分享中的保密性,艾森豪威尔回答道:“同盟只有通过信念和信任才能维持。”他强调“在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信任和信心来指导我们,而不是试图事先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不应该像律师那样斤斤计较”。
那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忧虑是真的,而艾森豪威尔却是在诡辩。因为到了1956年末,“事实上,政府已考虑更加近乎全面地将核武器的控制权转让给盟国了”(John D. Steinbruner, 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naly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75)。在那年底,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都提议美国向北约国家提供核武器(的使用方法)的训练,以及在紧急时刻把核武器转交给他们使用。1957年初,美国同意按照双重钥匙制向英国转让一部分中程导弹。所谓的双重钥匙制,指的是盟国拥有核武器的投递系统,同时,美国将保留对核弹头物理上的保管及在发射问题上的否决权(当然英国也有否决权)。英国当然只是一个突破口,艾森豪威尔真正想做的是在整个北约内普及这种做法。该年4月,艾森豪威尔建议向北约其他盟国提供类似的安排。同时,还向法国、意大利、挪威、荷兰等国提供帮助,协助它们生产可以用于发射核武器的装备。
在艾森豪威尔所推行的各项核分享政策中,形成制度,维持时间最长(一直到现在),也最有影响的政策就是双重钥匙制。从1957年起,美国同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希腊、联邦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土耳其九个国家签订了此类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了战术核武器、短程导弹和中程导弹。

1961年,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一百多枚能够用核弹头打击莫斯科的美国导弹。
虽然从名义上说,这些储备在盟国基地中的核武器仍然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但实际上却不然。1960年11月到12月,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对各欧洲基地进行了一次访问,视察双重控制协议的实施状况。1961年2月份,他们在给新任总统肯尼迪的报告中,认为美国实际上放弃了对其核武器的控制权。在内部会议讨论中,他们痛骂艾森豪威尔把核武器到处乱送。艾森豪威尔所签订的双边核合作协议未经国会认可,是非法的,而且当初这些协定只是说提供培训用信息,而不是用来建立一支导弹核力量。议员们声称,并非欧洲国家乞求美国政府给予他们核武器,反而是行政机构主动将核武器强加于人,不管他们是否适合接受这些核武器。议员们对美国核武器保管的松懈大为吃惊,“负载着核弹的战斗机停在机场跑道的边缘,德国飞行员端坐在驾驶舱内,开启的钥匙插着。代表着美国进行控制的具体化身,是一个美国军官,站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握着把左轮手枪。这个小伙子甚至不知道如果飞行员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强行起飞他应该朝什么开枪”。在另外一个地方,美国的核武器直接装配在外国导弹上,“旁边站着的七个人(带着一辆便携式拖车,电源接在核弹头上),其中六个人是外国人,代表美国行使控制权的是一个美国人,由他带着核钥匙。那些人如果想要拿到钥匙,只需要一棒子打在那个美国人头上就可以了”。由于核武器实际部署在欧洲盟国的基地里面,只由少数美国士兵负责保管,因此所在国想要实际夺取美国的核武器,只是“几把扳手的事情”。
当时美国驻欧洲的空军司令兰登也有相似的看法。“理论上说,这些核武器在我们手中”,但是由于盟国的飞机要接受使用核武器的训练,因此“我很确定我们违反了1到13条规定,也许更多”。艾奇逊在1961年也评论道,“许多欧洲盟友的军队——特别是荷兰、意大利和法国——实际上持有核武器。”“美国对这些武器的控制,在很多情况下仅限于理论状态。”(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195)
有很多证据表明,这种管理和控制上的松懈是艾森豪威尔有意为之的结果。1956年底,在会谈中美国向英国官员暗示,不要过于把美方的监管规定当真。英国官员向本国报告说,“根据他们的原子能法的规定,核弹头从技术上来说应该由美国来保管,但是我明白这样的要求可以通过驻扎少量军队军械人员来绕过去。” 1957年12月,美国副国防部长向法国领导人保证,“(核弹头)技术上来说留在美国人手中”,但是一旦发生战争,这些弹头“立即可得”(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198) 。1959年6月,艾森豪威尔对诺斯塔德说的就更加直白,“我们真心诚意地交出对核武器的控制,我们将仅仅保留名义上的所有权”(Steve Weber, Multilateralism in NATO: 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 1945-1961, p.56)。
不过,艾森豪威尔的首选还是让欧洲拥有一支统一的战略核力量。在1957年5月,美国国务院建议同北约其他国家签订多边协议,建立所谓的“北约核储备”。到了1957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会议上,“北约核储备”计划成为美国的正式提案。1959年12月6日,欧洲盟军总司令诺斯塔德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第四支核力量”的说法。他说:“我们怎样去满足我们欧洲盟友的愿望呢?这种愿望在日益增长,但仍然有点混乱,而且自相矛盾。它们的愿望就是要求更多地分享对核武器的控制权。怎样才能使作为整体的联盟放心,这类武器会在一切适当的情况下提供给他们,用来保卫它们,保卫欧洲呢?”答案是:“如果政治上可行的话,那么把原子武器的使用权更直接地交给集体意志去决定,这种行动会是一个重大的新步骤。”(G.巴勒克拉夫编:《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137-139页)这主要指的是让北约统一指挥一支中程导弹核力量。
1960年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提交了一份报告,也提出美国的利益仍然是欧洲的一体化,要确保欧洲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和美国一样承担起强大的领导角色。由于美国威慑能力的下降导致了美国承诺的可信性的下降,使得欧洲国家有离心倾向。美国的应对方案是使欧洲国家具有一支统一的集体核力量,从而解决可信性难题,促进欧洲一体化。该报告建议美国将五艘核潜艇永久指派给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指挥,美国承诺这种指派是不可撤销的,这些潜艇的操作人员将由多个国家的水兵共同构成。
艾森豪威尔对以上两个想法都表示赞同。他派诺斯塔德去游说欧洲各国,让他们接受这个“第四核力量”的想法。当时的德国总理阿登纳对诺斯塔德说“欧洲需要在核领域获得一些东西……以防美国领导层发生变动(而带来政策改变)”。诺斯塔德回答说:“美国人民不准备将核武器交给任何打算独立使用它的国家”,但是通过提供北约中程导弹计划,就能够提供一种最好的解决措施。
到了1960年底,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放弃多边核力量中美国的单方面否决权。该年11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名为《60年代的北约》(NSC6017),是对美国核分享政策的总结。该文件建议:一、美国正式承诺永久将一部分核武器指派给北约组织;二、美国可以提供(对使用核武器的)的事先授权。
七
纵观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他通过逐步渐进的方式给予了欧洲盟国部分核控制权,他转让了核信息,提供了运载工具,并实际在欧洲各国储备了部分核武器(约定可以共同控制)。他的梦想是使欧洲人具有一支独立统一的核威慑能力,使北约具有多个决策中心。
有两个因素使得他的梦想没有办法完全实现。
首先是来自美国自己。将自家的核武器拿来给别人用,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遭到激烈反对,美国也不例外。约翰·肯尼迪虽然自诩是新时代的人物,但他在国际关系上的态度其实比艾森豪威尔要保守得多。肯尼迪的传记作者西奥多·索伦森跟随肯尼迪十一年之久,先后担任肯尼迪的参议员个人助理和总统特别顾问,他写道:“实际的情况是,肯尼迪本人既不把大西洋联盟,也不把大西洋的和谐看作是目标本身。……他感到,当西方联盟已经不再……是我们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时,……我们的国务院的传统却还在引导我们从西方联盟出发来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每个问题。他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把联盟的其余国家同国会一样看待——即是一个必需的、但并不总是受欢迎的伙伴,他并不总能得到它的合作,他也并不总能接受它的意见,同它保持一种不愉快的关系似乎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表明的那样当他独力承担起责任时,他表现得最好。”(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391-392页)

当地时间1962年8月22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出席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
在1961年取代艾森豪威尔之后,他立即任命前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北约军事战略和美国的延伸威慑状态进行根本评估,评估的结果是,美国应该对所有北约核力量进行集中控制,一个扳机上只能有一个手指头。“对美国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军队对核武器的使用应该置于美国的否决权与控制之下”。所以肯尼迪的对应举动是收紧了双重钥匙制,往美国驻在欧洲基地里的核武器上装电子锁,同时修改艾森豪威尔的中程导弹计划,保留美国的单方面否决权。艾森豪威尔原本想让欧洲盟军司令部成为一个独立(于美国)机构,但肯尼迪明确否定了这一想法。
另外的阻碍来自欧洲人自己。拿英国来说,1960年在与美国的私下会谈中,英国表示希望能从美国那里获得核运载工具,但是并不愿意让其他国家通过北约框架指挥英国的核力量,也不愿意让欧洲大陆国家掌握中程导弹生产技术。因为他们害怕欧陆国家会不成熟地引发核战争,所以并不愿让北约发展战略核力量。英国反过来劝说美国保持对核武器的控制权,放弃更大程度的核分享,而改在北约的内部磋商程序上做文章来满足非核盟国的要求。
法国和德国倒是更热心一些,但是随着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欧洲国家之间的核合作的构想就被中断了。戴高乐想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欧洲,而不是欧洲的欧洲。他希望的欧洲是一个由独立的法国当头领导的国家联合体,而不是法国也混入其中的一碗欧洲汤。戴高乐虽然也要欧洲成为美苏之间的第三力量,但是在他心目中,这样一个第三力量的组成应该像十九世纪初维也纳会议后的德意志联邦,而法国就是这个联邦中的普鲁士。既然做不到这点,戴高乐宁愿选择光荣孤立,他放弃了法、德、意核合作协议。1963年1月,他又断然拒绝了肯尼迪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他认为,这个计划要求法国放弃独立核力量,由美国提供北极星导弹,但只允许美国人来扣动核扳机。
总之,欧洲人自己对“欧洲核力量”也抱有相当的怀疑态度。
以上两个因素——美国想继续做老大,欧洲不愿独立——共同扼杀了艾森豪威尔的北约核力量构想。
八
但艾森豪威尔还是成功了。如果说他想从欧洲抽身的计划并没有完成,但他确实垒实了北约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在部分程度上消解了北约的核困境。
是的,美国给予欧洲国家的安全保障仍然是不确定的,但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一个动作——核分享——显示出了美国承诺的部分可信度。
首先,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从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部署在欧洲国家的那些核武器其实就是一种抵押。基辛格曾经说,美国在欧洲的驻军相当于欧洲人的人质。美国放在欧洲的核武器又何尝不是呢?正是由于这种抵押的存在,使得欧洲国家更容易相信美国人的安全保证。其次,核分享也不仅仅只是一种抵押,也是一种姿态。从披露核信息开始,接着提供核训练,再接着提供核运载工具,再接着按照双重匙制向欧洲国家提供战术核武器的部分控制权,再接着企图使欧洲国家具有中程导弹能力(生产或者由美国转让),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是在冒险进行信任建设,而这种冒险自然有它的声誉价值。
我们怎么评价艾森豪威尔的这种行为呢?他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是的,艾森豪威尔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他曾多次对人说,“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我们的盟友”。他坚信,为了使盟友乐于贡献,必须使之摆脱二等公民的地位。为了使盟友成为真正的伙伴,就必须给予他们以一定的自主权。基辛格在描绘北约内部关系的时候,说:“自相矛盾的是,大西洋地区的团结可能要依靠这样一种治理结构来促进,这种结构给予各国自由行动的空间,但是减少它们如此行动的欲望。”(Henry A. Kissinger, “Coalition Diplomacy in A Nuclear Age”, pp.541-542)这就是艾森豪威尔想要达到的效果。
但是艾森豪威尔在这么做的时候,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核分享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欧洲国家建立独立国家核力量的打算,从而保护了核战略决策的集中统一性,而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他敏锐地发现,在欧洲独立国家核力量与美国的核垄断之间,存在着一些可以妥协的空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艾森豪威尔的核分享安排是带有一定模糊性的,盟国到底能不能完全控制美国分享给它们的核武器,是没有确定答案的。即使艾森豪威尔自己,也说美国要保持名义上的所有权。这种模糊性可以用来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对美国国会,艾森豪威尔可以争论美国仍然监管、持有这些核武器;对盟国,艾森豪威尔可以暗示在必要时美国将转移核武器给它们,使之拥有核威慑能力;对苏联,艾森豪威尔又可以展示说,美国的核分享在“有无之间”,既隐隐带有核威慑,又不至于太过刺激,从而引发苏联人的过多担心。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能看到机会,发挥想象力与才能,使之实现,从而为他人,也为自己赢得创新利润。在市场上,我们称这种人叫企业家。在政治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政治企业家”这个概念,这指的具有强烈的制度创新偏好和一定利他主义行为特征的个体或组织,他们能看到一群个体有对某公共物品的渴望,并通过制度创新为大家提供这一物品,间接为自己牟利(Philip Jones, "The appeal of the political entrepreneu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4 [1978]: 498-504)。
政治企业家有如下特质:一,他/她具有一定的远见,能够超越自己暂时的短期利益考虑;二,他/她宁愿承担不可预知的风险和与其预期收入不成正比的创新成本。当然,我们并不能把政治企业家等同于“好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可能是,他/她善于捕捉制度发展的机遇,并甘于做出牺牲,以换取长期更大的利益收入流(这种收入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如声望与尊重);三,他/她有一定的创新偏好,能够把握时机;四,他/她也能够有效地动员、监督其他个体参与新制度,分割成本,分配利益;五,他/她能让其他人相信其推行计划的稳定性,建立自己的信誉。(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65-193页)
从上面的说明来看,艾森豪威尔能够称得上是北约核关系上的政治企业家。
最后让我们简单对比一下艾森豪威尔与特朗普的异同吧。两个人都想从欧洲撤出,减少美国的国际责任,艾森豪威尔一直坚信美军在欧洲的存在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他在担任欧洲盟军总司令的时候就说过:“如果在十年内,所有驻扎在欧洲的美国部队没有返回美国,那么整个计划(指的是北约)就是失败的。”(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p.148)但艾森豪威尔与特朗普不同的是,他并不简单地看待这个目标。他认为,长远来看,维护联盟的稳定符合美国利益,即使这意味着分享部分权力和资源。他增加而不是削减对北约的支持,主张更多的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他让盟国“占美国便宜”,并认为让出这些“便宜”有长远价值。
一位美国牧师沃伦·威尔斯比(Warren W. Wiersbe)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实主义者是历经劫难但被烈火洗礼的理想主义者,怀疑论者是那些没有挺过去的人。”艾森豪威尔就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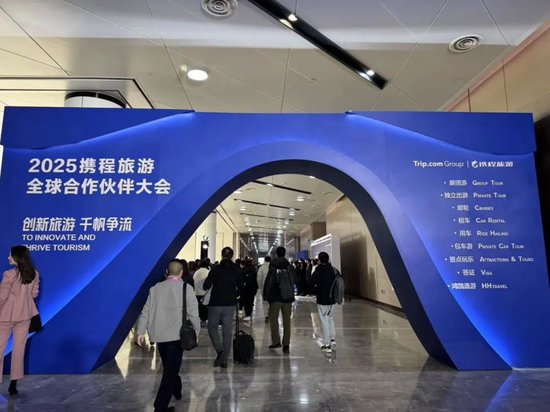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