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摘要:
... K和意大利人约好,大约十点钟在大教堂碰面。
“K准时赶到了。他进来时,时钟正好敲响十点,但是客人还没有来。”(韩瑞祥译本)按照有一种解释,这里“时钟正好敲响十点”应该根据卡夫卡的手稿改回原样:“时钟正好敲响十一点”(Idris Parry译本)。
据说,这是因为在小说中,K的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本来就是不一致的,相差一个小时。当K自以为是十点钟准时赶到的时候,公共时间其实已经是十一点了(是时钟敲响了十一点,不是他自己的手表指着十一点。他的手表在许久之后才指到十一点,所以按照卡夫卡的手稿原样,K的时间比公共时间晚一个小时)。他迟到了一小时,客人不是没来,而是已经走了。
这个解释进一步把整个“在大教堂里”的时间都解释为迟一个小时:这一章说K在这一天一大早——七点——就到了办公室,但这是K自己的私人时间,实际上已经八点了;当九点半K急忙要赶去教堂碰面的时候,这个九点半也是K的私人时间,实际上已经十点半了。解释者把这个现象解释为“落后于时间”。
但是,这里存在显而易见的困难。
首先,意大利人与K约定时间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的“十点左右”,而是“两个钟头后,约摸十点左右”。如果K是按照“十点赴约”来安排时间的,那么在他们约定碰头时间的时候,K的表和意大利人的表必定是能够对上的——都是八点——否则“两个钟头后,约摸十点左右”这两个参照点中,总是会有一个参照点不能满足。
其次,这一章说K七点就来到办公室,本想在会见客人之前处理几件事情,结果意大利人客人已经来了,他的时间就被占去了。这段提早的时间在经理和客人你一言我一语中消磨掉了,K“不知不觉坠入朦胧之中”——他走了神,几乎忘记自己是在陪着客户,竟然想站起身来离开,“幸亏及时如梦惊醒,吓了一大跳”。这时,“客人终于看了看表,猛地跳了起来”。似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然后又是交谈,才商定了“两个钟头后,约摸十点左右”的时间。在K到达办公室,并且消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时间才到八点。这两个理由似乎应该能够说明,K的手表本身并不落后于时间。
K起初不可能是一个落后于时间的人。他的表必定是准确无疑的。否则他无法在一家大银行凭着自己的能力升到“襄理”的职位。但从他牵涉到法院程序的那一天起,只要是跟法院打交道,他就总是要迟到一小时。
三十岁生日这天,他莫名其妙地被逮捕。逮捕是在公寓里进行的,在K看来就像恶作剧一样。逮捕程序耽误了上班时间。K准备赶去上班的时候看了看表,“已经迟了半个钟头”。等K打车来到银行时,他就已经迟到了一个钟头。因为,我们可以根据第二章中的叙述推断,K的寓所与银行之间相距半小时的车程:他在银行待到九点然后直接回家,到达公寓的时间是九点半。
初审是在一个星期天,通知却没有告诉K具体时间。K决定赶在法院平常上班的时间,也就是九点。他九点准时到达了。但法庭设在居民公寓楼不知哪个地方,所以K花了许多时间、费了许多功夫找,几乎挨家挨户地找,终于在阁楼找到审讯室。结果他被告知,他已经迟到了一小时零五分钟。
审讯室的设置属于整部小说精心设计的一个部分:法院程序全部发生在私人生活空间内部:逮捕是在公寓住户的房间内执行的;对违反规定的看守执行的鞭笞之罚是在银行的小仓库里实施的;律师在被窝里接待委托人,委托人睡在律师女佣的房间,以及最后大教堂和神甫也是法庭的一个部分。假如像K说的那样,大教堂里的神甫是监狱神甫,那监狱就设在大教堂。总之,法庭系统中整个最低层级的设置,都深嵌在私人生活空间的内部,彼此不分。
假如我们接受对手稿的改动,“时钟正好敲响十点”而不是“十一点”,在大教堂里,K仍然迟到了一小时。应该注意到,虽然经理声称K的意大利语很好,但实际上,K完全听不懂经理与意大利客户之间的谈话。是通过经理的嘴,K才知道有关意大利人的行程安排和参观要求的。这很可能意味着,“两个钟头之后,约摸十点钟”在大教堂见面的计划,是经理的安排。
至于意大利人,K其实完全不清楚他的行程。这等于说,交谈只存在于经理与K之间,以及经理和意大利人之间,而这两个交谈之间,其实并不存在能够为人所知的关联。三个人坐在一起,因为语言不通,同时展开了两个不同的对话。是经理引导K去了教堂。时间是十点,而意大利人没有出现。十点,并没有迟到。但K见到神甫时,已经迟到了一小时:他的手表显示,已经十一点了。
我猜测,这个十点正是神甫要求的时间。经理是神甫的帮手。由于K似乎理所当然地知道神甫是属于法院的,因此,经理其实代法院下达了传唤的通知。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到另外一个情节:经理很可能一开始就是幕后的知情者和法院的辅助者。在被逮捕的那天早上,与看守及监督官一起出现在K的公寓中的,其实还有三名银行同事。K见到他们时起初完全没有认出他们。这暗示,诉讼程序最初启动之时,银行就已经知晓并介入其中了。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经理在安排并鼓励K去陪同意大利人参观教堂的时候“一脸愁容”。他想讲明原委,却又最终“没有说出确切的缘由”。是否可以推测:经理知道K此去其实是去领受他的判决的?这个推测呼应了神甫的话:“是我叫你到这里来的”。既然只有经理让K前往教堂,那么经理自然是在执行神甫的委托甚或命令。
结论很可能是这样:神甫/经理要求K十点到达,K准时到达了;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人客户的事上,结果因为寻找和等待意大利人而耗费了一个钟头,直到十一点才与神甫见面。如此一来,也不再需要解释意大利人是否已经来过。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在教堂出现。
总是迟到一小时。这同K手表指示的私人时间准不准无关。卡夫卡可能在琢磨,最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并提醒读者这个时间问题。他似乎并没有找到满意的方案:时钟敲响十一点,这样设计最为醒目,最为不可思议,从而也可能是最富有解释深度的,但那样会引起一连串的计时问题。
对于一份未竟的手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无力也不宜走得过远。能够确定的是:自从被卷入诉讼,K与当局那神秘莫测的权力打交道时,就陷入了“迟到一小时”的困境之中。这迟到的一小时,对于K来说,究竟是多出了一小时,还是被剥夺了一小时?很难说清楚。因为这个一小时,似乎没有在程序上产生或好或坏的后果:工作照常,初审继续,而神甫对K仍然是“最好的”——K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这么说,这迟到的一小时几乎就是被无意义地消耗掉的时间。但它又是绝对必需的:只有耗去这一个小时,K才能达到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地点,接触与他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的人物。从这个角度出发,不妨把这“迟到的一小时”理解为不可见的至高权力给它的子民创造出来的一种生存处境,我称之为“必要的徒劳”。
它是“必要的”。因为K无法置身事外:每一件诉讼始终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个人的,K的诉讼就只是针对K的,是专门为K运转着的。所有的被告似乎都因此而为他们的“诉讼”付出了全部精力。作为与“新人”K的对比,商人布洛克,一位卖掉了自己的生意并且几乎住在律师家里随时等候会见的诉讼当事人,把这种“必要性”具象化了——K必须在这迟到的一小时里紧赶慢赶。
与此同时,它又是徒劳的。因为运转诉讼程序的权力并不是为某一个人特设的,它其实与任何一个个别的人都无关,甚至与每一个具体的官员都无关:在无穷的诉讼环节上,对于最终的裁决,“连法官们都无法摸得透”,更不要说当事人自己了。
用“迟到的时间”来表达这种徒劳,也许正是卡夫卡的匠心所在。果然如此,那么“迟到的时间”就同“在法的门前”的故事存在内在联系。在那个堪称神来之笔的故事中,有一对矛盾:法的大门永远向所有人敞开;但守门的看守最后对那个一生想要进门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人说,法的大门是专门为他而敞开的。
诉讼程序——这也是《审判》这部小说题名的字面含义——正是这两个矛盾的“命题”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结合的效果,在法学博士卡夫卡的笔下,凝结成一种“必要的徒劳”。无独有偶,另一位比卡夫卡更年轻一些的犹太人——瓦尔特·本雅明——后来在《对暴力的批判》中所批判的,同样是这一对矛盾命题的结合,并且可以说,他的批判与卡夫卡的小说异曲同工。
那么,什么样的权力在运转着这种诉讼?什么样的权力是它所统治的对象始终无法接近的?始终无法接近——正是因为如此,K才总是迟到?在小说中,这权力的化身是“最高法院”。但我们并不知道这“最高法院”是否就是我们熟知的“最高法院”——在小说中,“最高法院”没有地点。
-----
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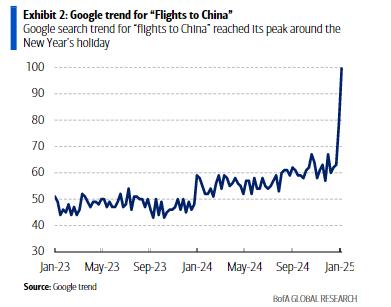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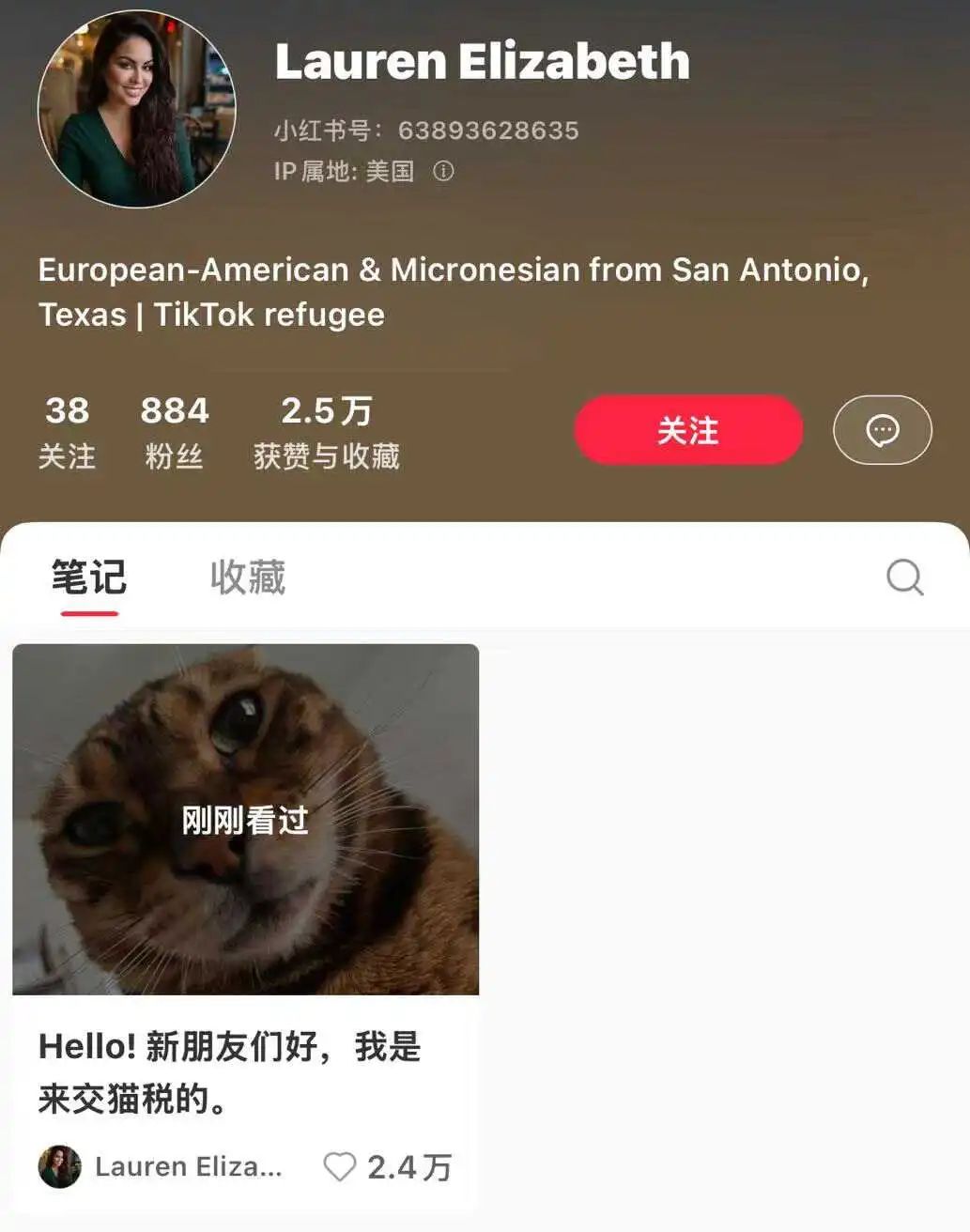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