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摘要:
... 为2024年经眼的几种中文书分别胡诌了几句读后感(不是所谓的“盘点”),勉力凑成一篇稿子时,题目却成了拦路虎。转念一想,小文提到的著作都跟历史有关,可以说它们各自呈现了历史的一种面貌。渡边一民《林达夫和他的时代》注重的是思想的“时代感”,张洪彬《祛魅》则围绕宇宙观的剧变深挖历史之井;王东杰《乡里的圣人》可以看作“边际书写”(比如日常生活与思想、身体与思想),李礼《古今之变》则通过访谈呈现历史的紧张与魅惑;岱峻的“发现李庄”系列更是亲自走进历史现场,打捞历史的声与影。所有这些通过各种媒介辗转交错传递到读者那里,定然会触动我们与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发生绵绵无尽的对话。
《林达夫和他的时代》,渡边一民著,伏怡琳译,王前审校,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

《林达夫和他的时代》书封
本书开篇(即序章“两名留学生”)以哲学家三木清(1897-1945)和历史学家羽仁五郎(1901-1983)为中心,勾勒了1920年代日本的思想氛围。书中指出,对西方而言,1920年代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对日本而言,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是一大劫难,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20年代成为“近代以来,经验乃至问题超越国境、显现出同步性与国际性的最早的一个时期”(23页)。大地震让日本人对经历过一战的欧洲人产生了“共鸣”,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几乎同步被引入日本。开篇聚焦三木清和羽仁五郎,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扮演了“西潮”引介人的角色。另外,这两人和本书的主角林达夫(1896-1984)共享同一个身份——创造型编辑,他们都为1920年代末岩波书店的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一章“同路人”首先讲述了发端于1926、1927年的出版革命,介绍了所谓“岩波文化”,然后着重分析了林达夫和三木清的作为。书中强调,林达夫和三木清都是“教养派”的典型,但又将两人分别戴上了“南欧系”和“北欧系”的帽子——前者崇尚“韵味”,作为文献学家的林达夫学识渊博,属于“南欧系”;后者追求“深刻”,偏好刨根问底,穷究事理,符合三木清的个性,故属于“北欧系”。
本书认为,1935年前后是日本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转折期,为此列出了三部完成于1935年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岛崎藤村的长篇小说《黎明之前》、和辻哲郎的《风土》和西田几多郎的《哲学论文集第一卷》。这三部著作“都与动荡不安的时代保持了一步之遥的距离”,“可以说它们都在努力回应明治以来‘日本与西方’这一根源性问题”(103-104页)。作为参照,第二章(“一九三五年前后”)也叙述了羽仁五郎的学术研究。
第三章“园艺与筑城术”指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达夫在两三年时间里倾注所有精力构建与国家对峙的个人堡垒,“具体来说,从实践园艺到广罗文献,当然也包括写作”,“这些作业便直接意味着林达夫对时代的反抗”(152页)。作为对照,“西田几多郎的思想在政治面前低了头”(159页),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在蛮横的时代“始终肯定国家的政策,全力对其进行理论武装”(162页)。而三木清和羽仁五郎“直到这一时期仍在各自的阵地上拒绝使用奴性的语言”,到了别无选择之际,则“选择了沉默”(167页)。
第四章“历史的黄昏”开头指出,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西欧精神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唯有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1902-1983)“清晰地阐述了此次事件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崩溃”(173页)。在如此晦暗的时势下,林达夫坦言已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不愿受人蒙蔽。也不愿蒙蔽他人。我尝试韬光养晦,可事到如今连哪些朋友与我同心同道都已分辨不清……”(178页)于是,林达夫进入了四年零十个月的沉默期。
第五章“隐藏的‘战后’”讲述了林达夫在战后的经历。在个人职业上,林达夫先后在中央公论社、角川书店任职,而后转入平凡社,主编《世界大百科事典》。在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林达夫自称“伊壁鸠鲁主义者”,寓居一隅,不参与政治,但同时也是世界主义者,仍然观察和思考着世界局势和思想动态。
与第五章详细分析林达夫的《反语的精神》和《忆三木清》一样,第六章“一九五〇年前后”也分析了他的《新时代的开幕》和《共产主义者》两篇文章。书中认为,《新时代的开幕》是“林达夫自身的一纸败北宣言”,面对云诡波谲的“战后”,他再次陷入了沉默(275页);而《共产主义者》“从整体上对苏联提出了质疑”(292页),显示出林达夫的时代敏感和洞察力。
第七章“三种文艺复兴”主要叙述了作为学者的林达夫的晚年。对于战后的世界政治,林达夫一面痛斥现实,一面陷入绝望。1956年春,林达夫又回到了早年西洋学研究的起点——文艺复兴。与本书其他章节一样,这一章同时将渡边一夫、花田清辉纳入视野,将他们笔下的文艺复兴与林达夫的研究一同置于国际精神史的脉络,指出“这三种文艺复兴翻开了日本新时代思想的新篇章”(351页)。
在“末章”作者一方面指出林达夫是一个异类,另一方面强调他勇于不断质疑自己的思想,因此能摆脱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上面对本书内容作了极为简单的概括,从中可以看出林达夫的主要身份是学者型编辑,或者说是具有卓越编辑才能的学者,总之他在昭和时代的日本文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跟其他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林达夫自身的作品可能不算多,也没有留下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应该说要为这样一位具有很大影响力,但材料并不丰富的人物立传,绝非易事。不过,作者巧妙地采用了“林达夫和他的时代”这一题目,通过多重人物的参照,细腻的文本分析,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把握林达夫的思想动向,使全书条理明晰,层次丰富。
鹤见俊辅称林达夫“在日本论坛史上是日本知识人里错得最少的一位”,这当然是十分了不得的评价。不过,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林达夫的“沉默”——这种沉默不止一次出现,自是意味深长。窃以为,错得多、错得少恐怕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如何真正贯彻独立思考的精神。书中有一个片段——三木清遭旧友批判——令人动容,启人深思。批判的对错姑且不论,类似的遭遇恐怕是独立的思想家都会经历的,甚至可以说思想独立的必经考验。书中指出1930年代前后的日本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相信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沦为统治阶级的娼妇,要么与新兴阶级结合用力推动历史的车轮。”(89页)一介知识人要保持独立,所能做的大概不外乎旁观主流,拒绝合唱,带着批判的眼光考察动态,分析局势,包括沉默。——当然,其结局可能是寂寂无闻,众叛亲离,寥落一生。
张洪彬《祛魅:天人感应、近代科学与晚清宇宙观念的嬗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祛魅:天人感应、近代科学与晚清宇宙观念的嬗变》书封
毋庸赘言,这是一部涉及大问题的力作。
如所周知,传统中国的世俗秩序(“人道”)是以人们心目中的宇宙秩序(“天道”)为基础的,所以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明清之际士大夫有“天崩地解”的震撼,而到了晚清,更是“天翻地覆”,“道”随之亦不得不变。本书的底稿名叫《天变道亦变:晚清的宇宙论转变》,相比现题,似乎更容易捕捉其探索的方向。
本书开篇明白宣示了其研究旨趣:传统中国人对天、天道以及形形色色的人格神的信仰在晚清时代遭遇了怎样的挑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此,本书巧妙地安排了妇孺皆知的话题(彗星、求雨;地震、风水;疾疫、灵魂),选取富有意涵的案例(如1879年武都大地震,1875年同治帝墓地选址),加以细致的分析,通过天、地、人“三才”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深入讨论了近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变迁。最后两章“机械宇宙观之于基督教和中国宗教的不同意义”、“天演论之于中国宗教和基督教的不同意义”,更显示出作者兼顾中西的视野和雄心。
对我来说,本书的内容颇为新鲜,这从参考文献和脚注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文献我此前不曾关注,其中有一些虽然知晓(徒知其表),但不曾探究(不明就里)。也就是说,这是我比较陌生的领域。因此,阅读过程无异于一场“知识洗礼”。
从李天纲教授的序言和附录的两篇访谈,又可知作者的学术热诚,有此厚重之作,亦在情理之中,同时不免更加期待作者的后续大作。
王东杰著《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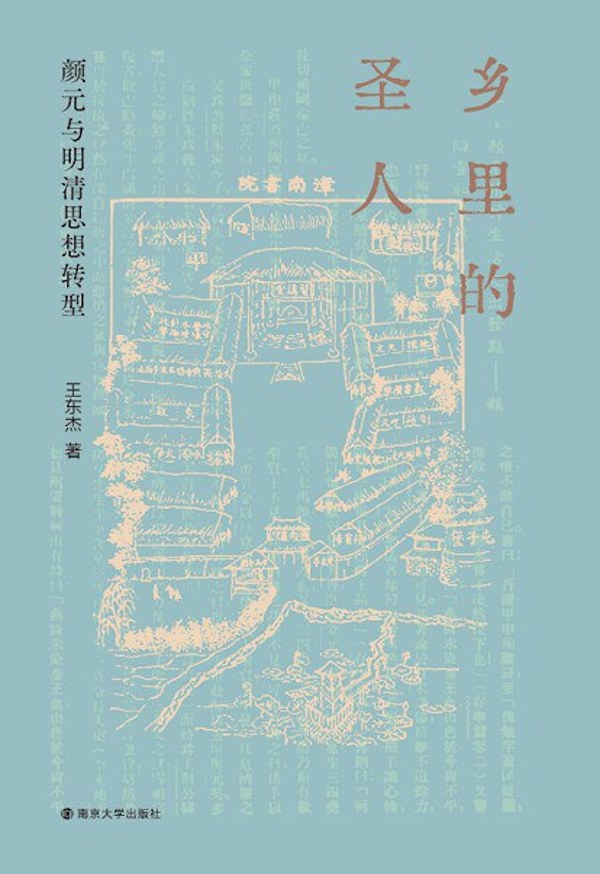
《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书封
该书篇幅不大,主体由三篇论文构成。第一章“血脉与学脉:从人伦困境看颜元的学术思想”借助“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和心理“创伤”这两个概念,对颜元的思想作心理史学的分析。书中强调身世之变与颜元的学术转向有着重要的关联。被谓身世之变,简单地说,出身河北保定博野县的颜元父亲幼年被邻县巡捕朱氏抱养,颜元四岁时父亲离家出走,在这种境况下,颜元自小姓朱,十九岁中秀才,取学名邦良,直到三十四岁时,颜元才得知自己的身世。三十七岁时,朱邦良改名“元”,两年后改组归宗,成为“颜元”,某种意义上这是颜元的“第二次出生”。五十岁时出关寻父,这“在颜元一生中,是仅次于身世之变的一场大戏,也是其一生事业的高潮”。总之,“对于把学问和生活打成一片的颜元来说,血脉意识和学统观念不但互为隐喻,甚而根本深入彼此的内涵:践行孝道既是在肯定自己的学脉,也是用实际行动维续儒家的道统”(88-89页)。
第二章“气质为何不恶:颜元的身体经验与思想构建”主要是诠释“肉身”与“道”的关系。书中指出学界总是聚焦于颜元的实践实行,而甚少关注他的气质论,接着提出有必要从“身体意象”(body image)的角度考察颜元的思想主张。围绕身体和疾病,书中讨论了身体与“成圣”的关系,颜元对静坐的态度,疾病与修身、学术转向的关联,身体健康与行医、习行六艺的关系。最后总结道:“只有颜元,以‘身体’这个概念为纽带,将所有这一切思考与实践综合在一起,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肉身’是怎样成‘道’,‘道’又是怎样化为‘肉身’的。”(148页)
第三章“在乡里‘作圣’:颜元与其乡人的互动”着重指出,“教化绝非只是精英对大众的单向施教,而是双方的相互影响。在一个讲究‘反求诸己’的思想体系中,面对他人的‘教化’与面对自身的‘修养’,是一个无法分割、相互促进的过程。”(149页)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章的讨论跟作者的实地考察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北杨村亲闻妇孺称呼颜元为“圣人爷”,从而意识到“作圣”的影响和意义不能局限于读书人的视角,还应考虑乡民的眼光。实际上,庶民百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圣人”的“教化”,同时还有“反-教化”——既有“反对教化”,也有“反向教化”的含义。
上述三篇论文可以分别看作生活与思想、身体与思想、思想的在地与互动的讨论。基于这三个角度的思想史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通过颜元这个历史人物做一番尝试,仍有其学术意义。
本书的导言“‘平庸’的思想者有思想史的价值吗”,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个问题(如何处理“一般思想者”的思想)仍值得探究。书中指出,“历史上绝大部分读书人都是如同颜元一样的,甚至是比他更为‘肤浅’的思想者。若以原创性与深刻性为标准,势必要将他们排除在思想史的论述之外。”(21页)的确,如果完全以原创性、深刻性为标准,中国近代思想史甚至无从写起,即使像梁启超、胡适这样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也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书中又说:“颜元的例子也让我们进一步思索思想的多样价值:言前人所未言,当然是一种贡献;但更常见的情形是,人们运用已有的思想,通过自身的实践和体会,使其焕发出(也许只有对个人才具有的)意义,后者同样是值得史家关注的。”(89页)一定程度上算是回答了导言提出的问题。
据此或可稍作引申,其一,像颜元这样重实践甚于思辨的思想者,自然不宜以思想的原创性与深刻性为准绳,而应从“实践”的层面捕捉和评估其在历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假如颜元绝对“平庸”,我们大概很难理解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会在学术思想史中给予颜元很高的评价了。反过来,从章、梁、胡等人对颜元的“再发现”来看,颜元的某些思想必然触动了他们的心弦和时代的神经,尽管后来发现包含了误读误解——比如将“礼教主义”的颜元说成是“反礼教”的(这也是思想史很有意思的课题)。其二,所谓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其程度和规模因思想生态的不同,有着巨大的差异。倘若追求康德那样的原创和深刻,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能达到标准的思想家,可谓寥若晨星。康有为、梁启超在晚清,陈独秀、胡适等在“五四”的思想冲击力有目共睹,但越过某个时段,冲击力便大不如前,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无可否认的。地域上也是如此。因此,思想史可以是涟漪状的,也可以是像路网那样交错纷繁的。
李礼《古今之变:现代中国的困惑——历史学家访谈录》,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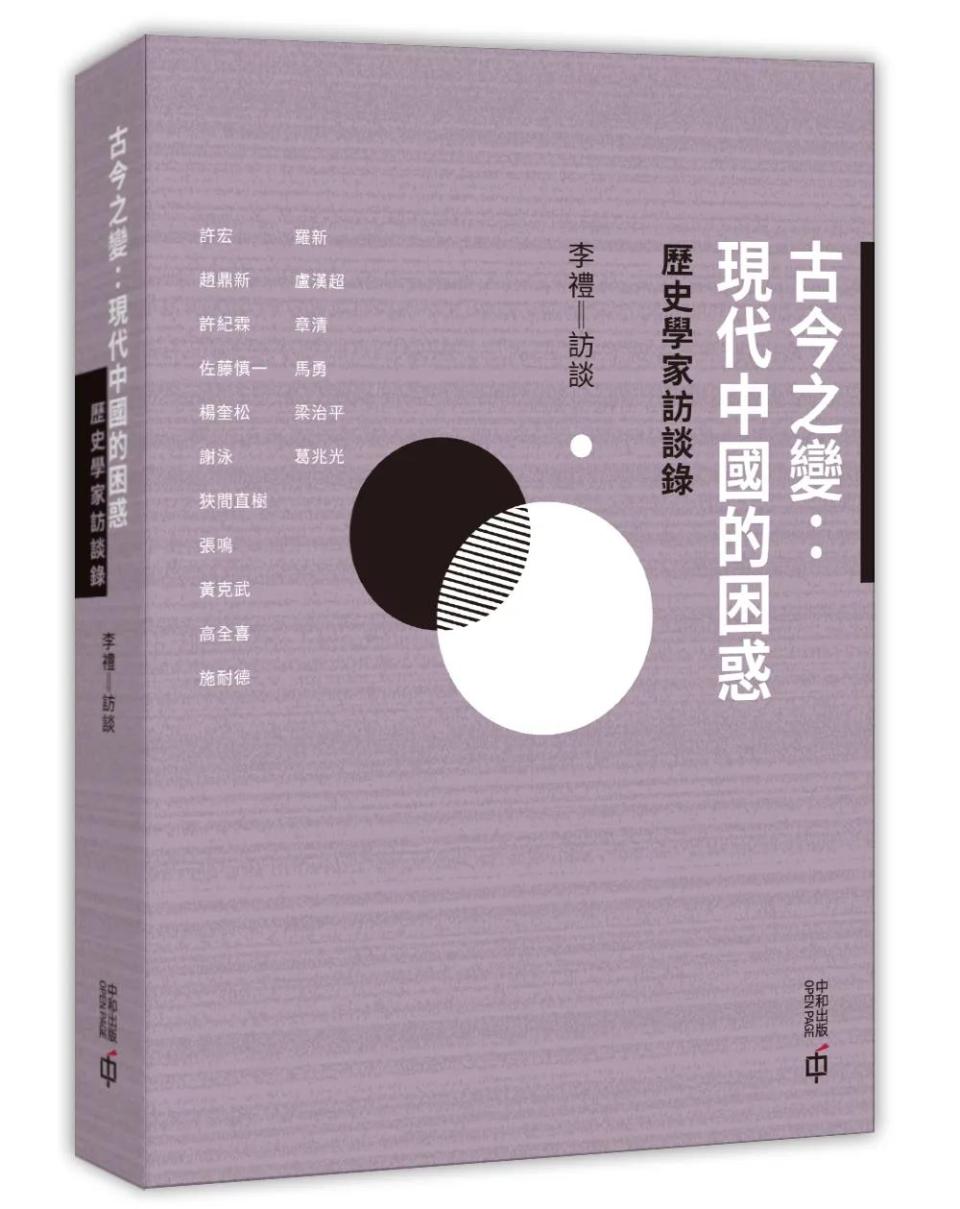
《古今之变:现代中国的困惑——历史学家访谈录》书封
这是一个访谈集,读起来很轻松,且颇受启发。其中,许宏、赵鼎新、高全喜三位先生的访谈,读后印象尤深。
比如,高全喜表示:“如果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来看,我觉得五四运动并没有全面代表启蒙运动,它没有达到这么一个高度。大家都知道民主与科学,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固然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但是问题在于单是民主和科学不足以建立起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法治宪政的问题就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短板,梁漱溟和章士钊当时就提出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夏勇先生曾经说,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赛先生”,还要提出一个“何女士”,就是人权,还要提一个“法先生”,就是法治与宪政。民主有它好的方面,但也隐含着很大问题,尤其是那种直接性民主,还有那种多数决的民主,一定要和法治宪政相结合。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民主新论》(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ed)非常好地辨析了民主和宪政民主两个概念的重大不同,民主是程序上的事情,但是未必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一群人可以干傻事。但是法治和宪政是有一些基本的自由价值,能制约民主中多数人干坏事或傻事的情况,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肯定是法治和民主结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民主是可怕的,而且是不可能存在的,那只能是古典社会,但是五四时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民主没有法治没有宪政,这就是它为什么越来越激进化。”
特朗普通过美国大选“二进宫”,现已众人皆知,而我观察日本政坛风云,也深切地感到民主应该成为重要的问题加以思考,而不是单纯作为信仰加以膜拜。只有对民主及其整体的社会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才可能真正把握民主、坚持民主,而不陷入乌托邦般的幻想——那意味着或大或小的灾难。
岱峻著“发现李庄”系列(三卷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岱峻先生于2004年出版《发现李庄》,此后两度再版(2009、2015年),加上《民国衣冠》(2012年),仔细修订,重新编排,再加上相关资料的发掘、整理,构成“发现李庄三部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这段史事的梳理和发现,嘉惠学林,著者的贡献再怎么褒奖也不过分。
抗战时期,有多家科研单位“漂泊西南天地间”迁入李庄,如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等。然而,这段历史长期湮没不彰。岱峻走入李庄,埋首文献,寻访乡亲和师友,以流畅隽永的文字、真切深沉的情意,使“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浮出水面,当年的故事和情感一扫空寂,惹人惊艳。
“三部曲”第一卷《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大抵脱胎于《发现李庄》,所以该卷算是《发现李庄》第三次再版,对照2015年版的目录,可知该版删削了一些内容,也增补了一些章节,结构更为均衡。该卷《前面的话》一上来就提出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行文则极为诚恳,比如作者表示:“《发现李庄》,发现是个动词,是不止歇的过程。”又说:“拙作《发现李庄》出版后,在收获肯定的同时,也遭致批评。”并以抗战时期同济大学教务长薛祉镐为例,坦承自己当年认识不足,虚心接受薛氏后人的批评。这样坦荡的襟怀,在当下学术界、文化界是不多见的。“过去的李庄,是由知道那段历史的一个一个鲜活的人构成的,随着它们的一一谢幕,那段历史在逐渐被风干,被形塑,或有些扭曲。”譬如,文中叙及作者与李霖灿之子李在中的交往和切磋,得知李氏辞世的消息时,作者发出悲叹——“呜呼,再没有可以和我辩难的朋友了”。凡此种种,交织成“发现”这个持续的动作,衍生出一幕幕历史场景。
如果说第一卷叙述的重心是那些机构,第二卷《一张中国大书桌》则可以说主要以人为视角,描摹山坳上学人的悲喜沧桑。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陈寅恪、梁思永、游寿、曾昭燏、庞薰琹、尹焕章、劳榦、向达、罗尔纲、王献唐……书中有家常琐事、私情恩怨,也有家国情怀,作者娓娓而谈,读来如在目前。许倬云先生读后,“既感亲切,又多感慨”。
与前两卷相比,第三卷《一本战时风雅笺》是岱峻“编著”的,封面上有这样一段“广告语”:“一场保存中华文化命脉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多种材料互证/另一个角度了解抗战之中国/大师诗词、日记、书信及回忆录/首次披露”。该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编 弦外遗音”收录了傅斯年、陈寅恪、董作宾、岑仲勉、陈槃、劳榦、王叔岷、梁方仲等数十人留下的诗篇,或咏山川风物,或状节令变化,或抒家国之感,既见文化底蕴,又见时代心绪。“第二编 六同忆旧”主要辑录了学人作于当年的文字,以及后来的回忆。“第三编 李庄飞鸿”则选录了寄至李庄和寄往外地的信函。细节丰满,文字生动,对于理解烽火弥漫之际的学术理想和学术命运,这些材料的价值不言而喻。
这套“三部曲”的写作自成风格,兼具可读性和学术性。文字之外,我想在此特别指出的是该书配有大量稀见的图片,这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当年学者的后人提供的,也有作者本人拍摄的照片、收藏的物件,弥足珍贵——擅于“读图”的读者一定能从中提取出人物风流和时代风云。所以,这样的历史画面搭配这样隽永的文字,真可谓相得益彰,图文并茂。
“自第一次寻访李庄发现李庄,转眼二十多年。那时我未晋知非之年,而今已逾古稀,黄昏薄暮,来日无多。但文本‘发现李庄三部曲’会留下来,会有更多的读者化为作者,汇入更多阐释、批评,进一步发现、充实。”这等令人唏嘘喟叹的文字是一位学者的付出和心血,是一段历史的复原和再现,是你我与过往的相逢和际遇。且读且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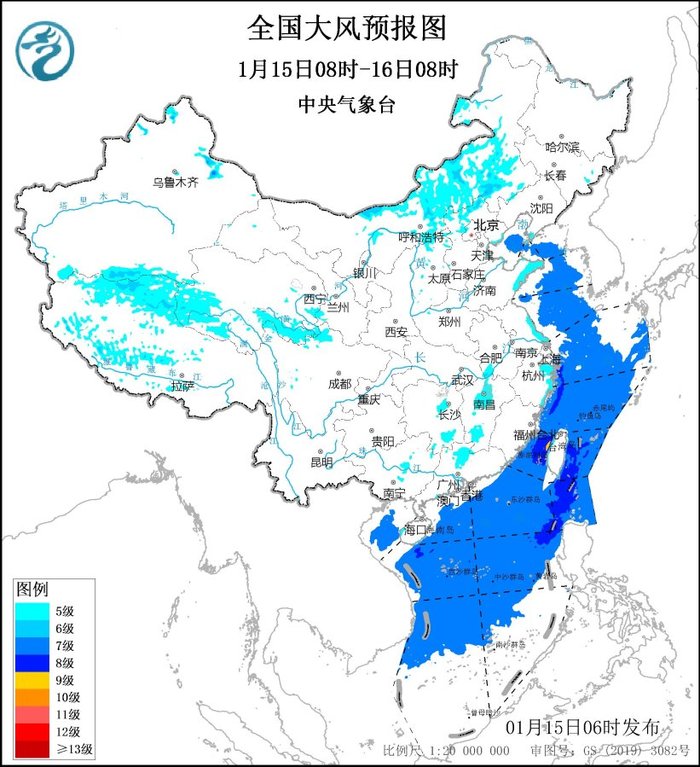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